|
正如裘小龙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,他是一个书生气很重、“有点迂”的地道上海人,去国多年,乡音未改,说话总带有一些上海口音。他笔下的陈超探长,早已是闻名西方的大侦探——裘小龙用英文写作的系列侦探小说,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,畅销数百万册。而他本人一直念兹在兹的,则是诗歌的写作、翻译与研究。早年他曾译过《四个四重奏》《丽达与天鹅》《意象派诗选》等,多年来一直坚持写诗,并痴迷于T. S. 艾略特的研究。时值他的诗集《舞蹈与舞者》与随笔集《外滩公园》出版,《上海书评》请他谈谈诗歌、翻译与侦探小说。 
《舞蹈与舞者》 
《外滩公园》 虽然您现在的身份是一名畅销小说作家,但是您特别喜欢诗歌,而且您的小说当中也经常出现各类诗歌文本。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您早年写诗、译诗的经历与您的侦探小说写作之间的关系。 裘小龙: 其实在你提问之前,我都没有怎么想过这个问题。现在想来,或许有几个原因。一个原因是我喜欢诗,但读诗的人不多,在小说里面放点诗,读的人就多了。这可能是受T. S. 艾略特的影响。他除了写诗,也写诗剧,其实没有诗写得好。他的初衷是,戏剧的观众肯定比诗歌的读者要多,用这个办法来扩大诗的受众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热过去之后,诗特别没人读。我把诗放在一个通俗的文类里,尤其是侦探小说这种文类,读者一下子就多了很多。 还有一个原因是,我最早用中文写作,后来用英文写作,但写的又是中国的故事,等于把许多东西混杂起来。我在想,自己能不能有意识地去做一点混杂的实验。我们都知道,中国古典小说里是有诗歌的,譬如四大名著。尽管我现在用英文写作,写的也并不是中国的章回体小说,但我考虑,能不能也把诗歌混杂进小说。我很喜欢莎士比亚将诗体和散文体交替使用的手法。在叙事的时候,必须有不同的抒情的强度,到了高潮部分,如果出现了诗歌,抒情的强度一下子就上去了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跟中国古典小说里诗歌的用法是不一样的。中国古典小说一般是每一章开头有一首诗,结尾也有一首,算是一种惯例。对我而言,诗歌是可以起到变换叙事节奏、调整抒情强度的作用的。有的段落特别需要抒情,我要么写一首诗,当然,是以我笔下的主人公陈探长的名义,要么翻译一首诗,选择的诗歌文本与小说情节氛围相符。这可能又是受到艾略特的影响,《荒原》就特别强调互文性(intertextuality)。我写小说的时候常常在想,这么多年下来,中国有哪些东西是变了的,又有哪些东西没变。我们乍一看好像发生了不少改变,但是认真端详,骨子里却又保留着原样。这个时候,如果能够恰到好处地引用一首古典诗歌,就有点像《荒原》里面那样——debunk,一下子拆台了,揭露了真相。 当然,归根结底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写诗。我不过是找一个理由,在小说里面满足自己的愿望。叶芝有一个理论,他说自己在中晚期的诗歌里,经常会采用一种戴面具的写法。诗里面说话的不是他本人,而是戴着面具的他。他想象一个人物,通过这个人物来写诗。我在小说里写诗的时候,就戴着陈探长的面具。他是一名党员干部,是一个警察,而我是一个比较书生气、比较迂的人。我们的身份完全不一样。他在案子里面经历的血腥的场景和残酷的政治斗争,是我根本不会经历的。他看问题的角度肯定跟我不一样,他写的不少诗也是我根本不会去写的。后来我在英国、美国、法国和意大利,都专门出过一本《陈探长诗选》,作者就是陈探长。这种感觉很奇妙,我最初不过就是想引用一些诗歌,烘托一下小说氛围,但是国外出版社不让我这样做,因为要付版权费,于是只好自己写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我的小说帮助了我的诗歌,我的诗歌也反过来帮助了我的小说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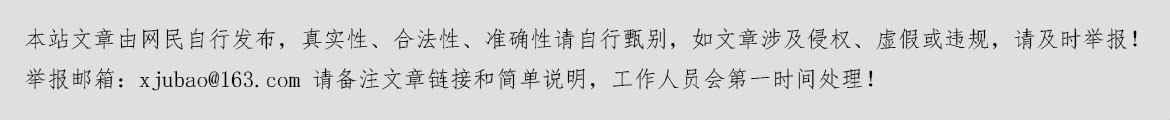
|
 鲜花 |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分享
邀请